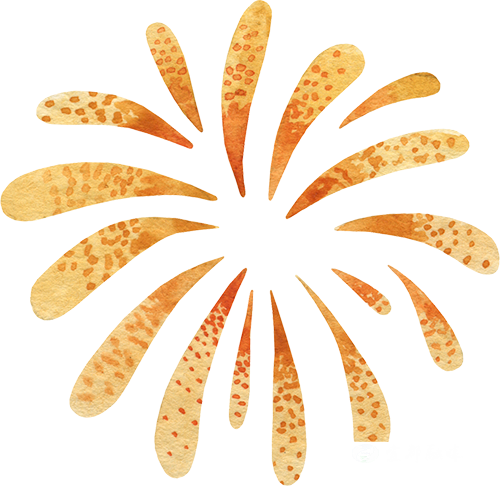
潘祖德

雪后山寨白茫茫一片,在金色朝阳映照下,反射出夺目的光。弯弯小河穿过积雪,犹如厚厚棉被豁出一道口子。不远处,几栋高矮不一设计精美的民房,已贴上春联、挂上红灯笼。戴红帽、系围脖的小姐弟,正小心点着地上的鞭炮。一侧房顶,升起缕缕炊烟……
“妈妈,这是哪儿的风景呀?”小伊可指着画夹问妈妈。
“这是乡下老家!快过年啦,谁不想家……这幅画带回去,作为新年礼物送给亲人,可以吗宝贝?”说着,母女俩相视一笑。
小伊可已是幼儿园中班的孩子。三年前因爸爸的工作调动,一家人迁居杭州。如今,妈妈也在一家服装设计室上班。平日休息,小两口带着孩子漫游周边景点;可静下来时,小淘气总是嚷嚷,缠着妈妈和照顾她的奶奶,要她们讲那些从前发生在老家的故事……

收柴垛盼聚财


伊可老家,位于鄂西南的大山深处。这里的秋冬季,远比山外寒冷,收柴垛自古成为山民的重要习俗,也是开启新年的序幕。
山村的柴禾堪比口粮,遇上天灾人祸什么麻烦,甚至比口粮更为紧缺,曾有闺女找婆家关注柴垛的事。一年上头,灶膛与火垄成为两张喂不饱的耗柴“嘴”。乡间老人知道,要是柴垛失火被焚,或者洪灾垛淹柴烂,农户想靠临时捡柴来吃到熟食那是很费劲的事。
直到改革开放那些年,不少山区仍重视村民积攒柴禾。每临秋后农闲时节,算计好的生产队长,会把握晴好天气,组织人马分做三件要事:一是搞好农田基本建设,如筑石坎、修路;二是上山砍柴,包括札柴和硬柴;三是下地种植油菜、洋芋之类的田间作物。
派工自然会量“体”用人。壮年男子大多被安排去干搬石、担柴的力气活,这靠的是爆发力和韧劲;手脚麻利的中青年妇女,多为砍柴捆柴的熟练工,山上的细活既要比技术,也要拼耐力,毕竟是以码好的个数计工;至于田里的农活,稍弱的劳动力都可以去干。
自集体林地分包到户,收柴垛的行当便成为村民自行打点的事。伊可的祖太和太爷,都是一方公认的收柴、摞柴高手。那些年,许多家庭缺少人手,收拾冬柴都需邻里互助择机行事。一两桌人上山,大帮小凑三五天敲定。所过之处,如屠夫宰猪去毛,除保留可用林木外,其余弱势杂木尽可收光,直到把山里柴禾转回来摞成垛为止。
旧时柴垛,是农家的温饱“防线”。一户一垛成常态;人多或富裕家庭,柴垛不止一个。柴垛的选址十分讲究,向阳、利水、拆取方便为最佳;造型也很别致,有方有圆,内松外紧,便于通风。柴垛大小不一,少则摞有一两百个捆好的柴禾,多则摞上三四百个柴禾。这些捆绑成个的丫枝柴,是由自然淘汰或病枯、倒伏的树枝,加上伴生的草灌藤木合成,每个柴禾重约二三十斤。体弱的人一担两个没问题,威猛男丁每次可挑四到六个柴禾。新鲜柴禾水分重,农户一般不急于转走,习惯先搁置在山坡上,等些天轻松点再担回去上垛。
山中栎树,木质细密,生长缓慢,是硬柴中最棒的柴禾,传统烤火炭就数栎炭价钱最贵。“除了栎柴无好火,拆开郎舅无好亲”,这是民间广泛流传的一句俗语。山区的栎柴,一般被锯成尺把长的短截,粗的还改劈成小块。寒冬腊月,行人路过见主人劈柴,大多会礼貌招呼一声“做过年柴”,主人便回敬一句:“年在您那儿呢!”
家中积攒的硬柴,有搁置在木楼的,也有顺墙码成一垛垛的。只要干爽不受潮,硬柴可放上几年,算得家庭的“硬实力”。鄂西方言,“柴”“财”同音,“栎柴”谐音“理财”。每逢除夕、新年对接的时刻,家庭主人会抱几大块硬柴进门,开口诵道:“财门大闸开,金银滚进来;滚进不滚出,堆上一满屋”,寄意年年财源广进。
收柴垛,是年的前奏,是生活的保障,也是财富的象征。

熏腊肉扫堂尘


无腊不成冬,无腊不成年。油亮腊肉,是冬春餐桌上不可缺少的美味。从古至今,山乡农家没有哪一户曾怠慢过冬熏腊肉。
小伊可家自然不例外。妈妈告诉她,自己小时候虽少吃肉,但特别爱闻腊肉香,感觉简简单单的腊味,就是原汁原味的年味。
冬腊风腌,蓄以御冬。现如今,每每入冬,家家户户会提前挪出一间相对低矮且密封的杂屋,主人在横木檩上钉钉子、系钩子,等年猪肉腌制一礼拜便出水挂上去熏烤。山地平原、城镇乡村,地域差别、风味纷呈。腊肉熏制技巧和方式各有千秋:有的撒盐多,有的用盐少;有的重麻辣,有的爱清淡;有的瓦缸腌,有的薄膜摊;但有一点比较统一,那就是都离不开烟熏火燎,而且,还普遍喜好加用松、柏、樟,或者柑橘、酸柚等树枝熏制增香。不紧不慢,十天半月之后,腊肉就会在时间和烟火的作用下,渐渐趋向黄里透红、自然芳香。
其实,过去乡下居住环境差、柴缺猪肉少,百姓大多烤火熏肉“一打两就”。寒冷季,烤火屋是使用频率最高的生活用房。
贫穷是多“症”联动的“病根”。缺粮养不出壮猪,“购留各半”熏不出几块腊肉,肉食歉收长不出健康汉子。仅有的半边猪肉,加上头蹄内杂,几日连熏黑不溜秋,极像“莲花闹”(竹板)挂在炊火钩上方的墙壁和木檩上。客人坐在垂悬的肉块下方烤火闲聊,除有落尘,还时不时遇上头顶滴落的盐水浸扰,以致宾主互为尴尬。
更闹心的是夜间鼠患,不问青红皂白,不嫌烟灰脏呛,择其精肉一顿猛啃。平眼一望浑然不知,待数日后发现,狡猾的鼠已在瘦肉“集中营”啖出一个大洞。饥荒年月,可怜兮兮,主人急得落泪。
伊可双眼扑闪,追问妈妈:“猪肉烟灰能洗掉吗,怎么才擦净屋子的黑东西呀?”妈妈一笑,“对啊,接下来就要扫堂尘啰。”
很多农村孩子见过扫堂尘,知道这是过年不会省去的大事,而且一年一次。每到这天,农家会以火垄屋、灶屋为重点,还要兼顾其他房间。主要任务是,把房梁上的烟尘、面墙蛛丝,一扫而光。

扫堂尘
扫堂尘一般选在农历小年前后。家庭主妇会提前动手,用细枝条扎成笤帚状,再绑上长长的竹竿。清扫之前,主人会全副武装,穿戴好罩衣、头巾,有的还用口罩或毛巾捂住口鼻,以防吸入扬尘。
扫堂尘,送走往昔纷扰晦气霉运,迎来新年的吉祥鸿运。
净静相依。一切准备就绪,静谧的山弯又炊烟四起。年近了,神兽们归“笼”,各家各户早已打开尘封的菜坛。鼎锅炖腊肉算是老家的标配佳肴。奶奶取下熏好的腊蹄,用砍刀分成大块,再将树纹般的红肉团洗净、浸泡,然后放进鼎锅炖煮,不久释放出浓郁的腊香和咕隆咕隆的沸泡声。小孙子憋不住,冒着口水在一旁紧盯着奶奶的手。奶奶忙碌着,一边往锅里添加山椒酱、干萝卜皮、枯豇豆这些家常菜,一边自言自语逗趣道:“小胖嘟莫嘴馋,腊肉炖好就上盘。”
随后,一家人围炉而坐欢声笑语,好吃好喝的堆满圆桌。尚未归家的子女,也在远方打开视频,吃着老家菜,惦念亲人愁。
熏腊肉,一半烟火,一半清香,是妈妈留下的年味儿。

三十的火十五的灯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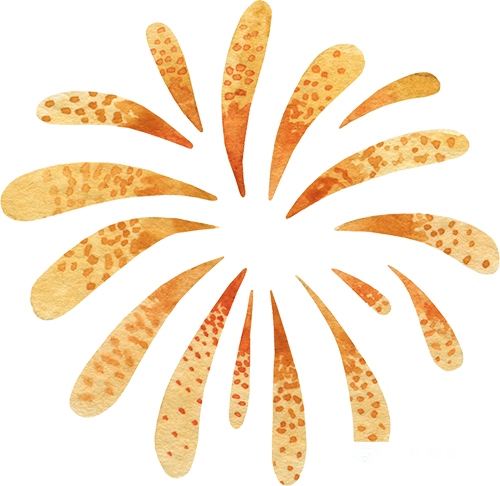
三岁的小伊可,曾回老家感受过一次除夕夜的氛围。不过那时候她的关注点,是玩扳鞭和小烟花,并不知熬更守岁、烤年火。
从妈妈那里,伊可总算听懂了一些,晓得除夕就是农历年的最后一天。一家人团聚吃年夜饭的印象,在她脑子里仍记忆犹新。
妈妈觉得不够,总想把山里老家那些过年的趣事儿,继续讲给小宝贝听下去。还打算找机会,带伊可回大山老家住些日子,沉浸式体验乡下腊雪、乡下美食、乡下年俗,包括三十的火十五的灯。
过去,民众大多习惯说“过年”“大年三十”“过十五”,却少有人称“除夕”“元宵”。其实,这与我国年俗文化普及相关。
步入信息时代,越来越多的人熟知以往没能理解的常识。比如农历十二月(腊月),大月三十天,俗称“年三十”“年三十夜”等;而小月为二十九天,有的称作“二十九暝”。这都算除夕,“除”字本义是“去”,引申为“易”,即交替;“夕”字本义是“日暮”,引申为“夜晚”。两字组词,便含旧岁至次夕而除、明日即换新岁之意。
旧时年夜守岁,一家人围坐火垄屋,谈笑间被大火烤得红光盈面。这是常见的情景。山民的火垄多为石制,造型也很别致,小户型人少的呈方形,大户人众的做成圆形或六角形,寄意阖家团圆。
古往今来,农耕文明赓续传承“火旺”习俗,认为过年“生旺火”象征未来兴旺发达、日子红红火火。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,《荆楚岁时记》开篇即有“庭燎”的记载,倡导烧火盆、点发宝柴,实则已将火垄视作一家人围聚的中心,已把熊熊火焰当作心中的图腾。
鄂西南山区,老辈农民喜欢在冬腊闲季,上山挖掘枯死的树蔸,方言称“打蔸子”。打蔸子需要蛮力,也讲技巧。浑身是劲的人,偏好大树蔸、老树蔸,一边刨土一边剁根,锄头、斧头、钢钎齐上阵,有时竟然要接连几天开挖才见动静。树蔸个大,百十来斤到几百斤重的常有,一个人搬不动,就请邻居帮忙抬回去。若是门窄了,还得进行二次分割,像代数里的因式分解一样,破大为小,化难为易。
到了年关,乡民处处图个吉利,说话也有禁忌。像吃猪舌头一样,“舌”与“赊”谐音,就要换说吃“赚头”;除夕烤火,火垄放进大树蔸,因“蔸”与“斗”谐音,这晚必须改叫烧烤“火猪”。而且,“猪”越大,火越旺盛,寄意家庭未来平安运和、招财纳福。
三十的“年火”必须备足,求的是旺而持久。家人围坐一圈,一边品尝雪枣、云片糕、杂糖、红薯条,一边盘算过去一年的收成,规划新年的愿景。直到子夜交替,新年“出行”的鞭炮声响起。
转眼正月行来,最有特色的年烟火要数元宵“上元”节了。
据传,主管正月十五“上元”的乃是“天官”。天官喜乐,所以要“燃灯”,意在新年带给人们新希望,素有“十五灯”之说。
元宵习俗由来已久,吃汤圆、挂灯笼,“送灯亮”“赶毛狗”,节日烟火精彩纷呈,折射古老前人尊崇二元结构中阴阳相对转换的生活理念。吃汤圆甜蜜老幼一家,期盼和顺团圆;挂灯笼彰显天地一体,追求自然和谐;“送灯亮”祭奠亡人,忆念世代恩情;“赶毛狗”,唱“灯歌”,放爆竹,体现惩恶扬善、化敌为友的民族价值取向。
伊可尚小,感觉有趣,却又像是听着“天书”。妈妈回过神来,牵着孩子的手,穿过客厅走向书房,然后推开窗门,指向远方告诉她:“今天老家又飘起雪花,好多亲人已开始忙碌年事儿。‘小天使’可见家家户户升起的炊烟——瞧瞧,是不是妈妈画的这样啊?”
小可爱望望画夹,再望望妈妈,似懂非懂地眨巴着双眼。


铭记,让历史成为永恒;体验,让传说演变为传承。乡土年烟火,已是走出去的无数乡下人,心中留存的那份美好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