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潘祖德
四季更替,旧颜换新;山河无恙,风光轮回。
鄂西南丘陵,跟江南平原和纵深推进的山地相比,地形起伏不大,温差变化柔和,空气湿度适中,植被换色频率略缓。
从儿时肩挎书包步行羊肠小道,到青春时骑车通过晴雨路上下班,再到中年驾车穿越乡村公路。数十年间,我的双眼就像单反相机镜头,无不感受和分辨着乡村弯弯的色彩差异。
山里的季节色装,最诱人的当属春秋两季。春季清一色下发“绿装”,犹如新兵的军装色调;秋季转配“迷彩服”,红黄绿蓝多色混杂,跟陆战队士兵出征打伏击的装扮差不多。

乌桕风景 图来源网络/侵删
千变万化的山川色彩中,虬枝盘曲且颜色光鲜的乌桕树,是我记忆深处水彩般的风景。那里除了故事,还有诗和远方。

如画乌桕 图来源网络/侵删
乌桕(音jiù),落叶乔木,是一种典型的色叶树种。每至深秋初冬,家乡昼夜温差逐渐增大,这树的叶绿体偏爱红蓝,绿色减退,红色加浓,树叶渐变如丹枫般红艳。
唐代“诗仙”李白留下“枫香乌桕两相依,红叶随风伤别离”的佳句,虽有伤感,却也客观存在;宋代诗人杨万里勾画秋山,写出“梧叶新黄柿叶红,更兼乌桕与丹枫”,另著“乌桕平生老染工,错将铁皂作猩红”的奇景趣诗。可见,乌桕美色早已千古留名。
早年,家乡乌桕漫山遍野,秋冬红叶随处可见。多数乡民不知学名乌桕,仅认俗名“木梓”。后查资料方悟,《本草纲目》描述“乌喜食其子,因以名之”,即乌鸦之类的鸟喜食其果实,故名乌桕。

野生乌桕 图来源网络/侵删
乌桕,乃家乡经济林木,亦为优良木材。因其属阳性树种,对土壤的适应性较强,抗风耐旱瘠,略具湿度,均能生长。
木梓花开初夏黄,状如毛虫蜜蜂忙。乌桕花朵虽小,却非常茂盛。老屋门前一株高大的歪脖乌桕,每到开花时节,相居邻里遍嗅花香,采花粉的小精灵忙碌不已,嗡嗡之音不绝于耳。风雨来袭,树枝摇曳,几日内乌桕花瓣纷纷坠撒,黑黄花尘密密麻麻铺满一地。
盛夏时节,乌桕树生长郁郁葱葱。重重叠叠的桃形树叶,在阳光雨露下,叶面大小和色素深浅悄然发生量变,公园、广场、道路旁等,不少地方时兴培育这种观赏植物。

乌桕树花 图来源网络/侵删
据说,乌桕叶还是黑色染料,旧时常用来印染衣物。
孩童好奇,爱采嫩叶夹于双手拇指间吹口哨,殊不知触碰乌桕叶片稍不小心,十有八九上当受“罪”。
原来,乌桕树是一种叫“洋辣子”虫的天堂,叶背面往往隐藏浑身长满尖毛的绿纹虫子。这种毛毛虫一旦刺蜇人的皮肤,瞬间伤处灼痛,数日后仍觉遗留的红痕瘙痒不适。

乌桕红叶 图来源网络/侵删
秋冬寒霜降临,乌桕红叶遍布。红叶开始从纷繁的美色群渐退,偶见三五片悠然飘落,离开多姿的树梢和串串“珍珠”木梓,犹如舞台节目和灯光色彩的自然转换。随后,进入短暂的采果时段。

乌桕果实 图来源网络/侵删
乌桕采果,家乡俗称“剔木梓”。乌桕树高矮不等,有的树干可达十余米。儿时瞧见户户备有剔杆,即选用数米长的竹木杆,细的一端倒装一锋利的月牙小镰刀。劳作时,顺着树枝缝隙,用剔刀瞄准连带果实的树枝向上削断,再把挂有桕果的枝丫一柄柄理顺捆好运回,利用农闲时在专用工具钉板上,像梳头一样清理果实。
散落田间地头的木梓粒,集体会动员老人小孩捡拾。“文革”时期,学校也会分季节组织勤工俭学。在瑟瑟寒风中,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漫山遍野捡木梓,带回学校称斤两、抵任务。
因为叶落籽出,油脂闪亮,遗漏在树枝或荆棘丛里的银色木梓,自然成为鸟类喜爱的食物。地面上红叶覆盖,小鸟扒刨,共享美食灵动跳跃,还竞相发出啾啾的低鸣。
乌桕根果都是宝,不识货的当柴烧。据资料介绍,乌桕在我国已有千余年栽培历史,其根皮可治蛇伤,果实乃化工原料。
乌桕果实分里外两层,一般油坊即可加工。其表皮是白色蜡质层,可提制“皮油”,用于肥皂、蜡烛等制作的原材料;里层的种仁,可榨取“桕油”(亦称梓油、青油),可供油漆、油墨等制作。就连乌桕果坚硬的粗壳(俗称梓壳),也是农家烤火的上好燃料。

乡土榨坊 图来源网络/侵删
上世纪八十年代,乡村还留有不少古式压榨油坊,乡村百姓习惯称油坊为“榨坊”。家乡规模较大的一家是柳树河油坊。
相距两三里地,有事无事我们爱结伴去榨坊游玩。在这里唯一能见到的现代机器,是一台个头稍大的老式柴油机;它卧立在榨坊里头的一个包间,通过长长的皮带,为整个加工车间传递动力。
睁眼所见的其他机械,几乎全是木质传动设施:顶上有径围很大的木齿转盘,带动一连串大小不等的圆木齿轮;经过逐一变速,终端的支杆发力,推动地上一米多高的大石碾,绕着直径约十来米的圆槽不停滚动,辗轧包括木梓等用来榨油的一切物资。
初加工完成后,还需进入更严格的手工流程。所谓“一坯二碾,三包四打”,就是老艺人对这一传统工艺的精辟概括。
一年中,除了夏季数月远远闻到菜籽油香,更多时候从榨坊飘出来的是加工木梓和其他油料的香味。
秋冬季节,掌锤的榨坊艺人衣着单薄,身裹一条粗大的吊八寸裤子,套一件糊满油渍的棉料背褂,紧握撞杆或吊锤,踏着节律般的步伐,退步、拖杆(锤)、推进,吼着号子对准靶向猛击。
一遍又一遍插着楔子,不厌其烦推拉对冲,榨筒越箍越紧,直至缝隙渐无。随着一阵阵沉闷的“咚、咚”撞击,金黄的油液缓缓流出。瞧着桶里积少成多,工匠们扯上毛巾擦汗,露出欣慰的笑颜。
室外冷风萧萧,坊内机器轰鸣、齿盘咬合、重锤敲打,与石碾咿呀组合,传唱同心圆“舞曲”。斜嵌灶内的一口大锅,师傅正忙着焙炒榨油的材料。全坊间热气腾腾,聚成一股共同缔造的磅礴力量。
隆冬时节,乌桕红叶全都华丽转身。一片片桕叶随风画弧,铺洒一地,为乡亲们默默渲染红红火火的年关底色。
老家门前的歪脖乌桕,退弃红装银籽,又派上新的用场。
冬腊月间,屋场邻居几乎全选在乌桕树下宰年猪。乌桕树横生一粗枝丫,最低处仅约一米七高,正好用来挂猪剁肉。
缺粮时代,老家的年猪不可能养得很肥,杀猪佬搭配一个辅杂工即可完事。宰猪剖腹取内脏,这是必经程序,家乡称之为“劈舱”。这脱毛去头,被洗涮得白白净净的“二师兄”肉身,经两人向上抬举,一点儿不费力,便将大铁钩倒挂于乌桕树的横枝上。
接下来是打开年猪腹腔。有点难闻的气味,屠夫总会先向里面泼几瓢清水,然后手脚麻利地清除心肝脾肾肠之类。这时,守在屠夫身边的,除了户主、杂工人员,还有小孩子和家犬。
主人候着,随时提供清理所需的用具,取走分离的猪油和蹄子。杂工负责拆洗肠子、清除内脏附着的杂物和积血。家犬紧盯着屠夫,随时准备抢吃剔落的废骨,有时还叼走落在地上的整块凝血。
孩子最关注的是猪“尿泡”(膀胱),充气后被叫作“尿气包”。过去的孩童玩具匮乏,平日里既玩不上篮球,也踢不着皮球,就连普通的气球都成为稀罕物,有时拾来气球的碎片也会玩上几天。
不知何时有人发现,猪尿泡清除尿液,置于草木灰中用脚反复揉踩,再充气会变得跟篮球一样又大又圆。
乡间孩子如获至宝,一时间“尿气包”成为他们的心爱之物。因这气包表面富含油脂,摸在手上不易清洗,加上漏气时还要用嘴补吹。宰年猪那些日子,乡下野孩儿满脸灰扑扑的,有的像包公,有的留下花猫样的黑嘴圆圈,甭猜十有八九是玩尿气包所致。
……
光阴如梭,生老自然。年长易恋年少事,忆及幼稚露羞涩。
岁月更迭,转眼又入新的轮回。以“春来江水绿如蓝”启幕,至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延续。不禁引人沉思:
绿动春晓,红叶秋韵;春花秋月何时了,往事知多少?
但愿,乡美人美,乌桕红叶年年可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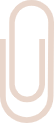

作者简介:潘祖德,湖北宜都人。湖北省学校文化研究会会员,宜昌市散文学会、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,宜都市故事学会副主席。勤于思考、勤于练笔,探访美丽乡村、感悟百姓生活;部分作品散见报刊网媒。
